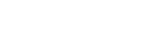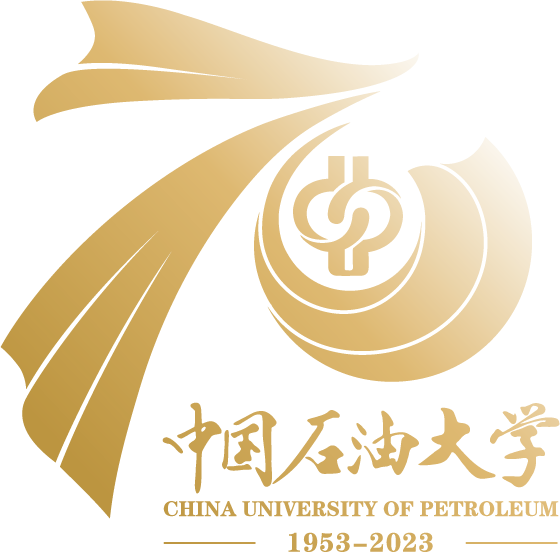一切都是瞬息,一切都将会过去,而那过去了的,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。
——普希金
(一)我与学院初相遇
1955年8月,我被北京石油学院录取,入钻井专业学习,这可是我报考的第一志愿大学的第一专业啊!
北京石油学院派到前门火车站迎接我们的,是井53级的学姐李妙兰。她操着一口亲切的“广式”普通话,短发,猴皮筋扎着两个小鬏鬏,一副假小子模样,英姿飒爽地把我们这批大学新生带上一辆没有顶棚的大卡车。卡车穿过大前门门洞后,景象豁然开朗,在见到日夜向往的天安门时,看到灯笼高高挂、红旗迎风飘的雄伟城门,我们不约而同地鼓掌!
卡车奔驰在长安街上,经西单,约40分钟到学院门口,便驶入用木板条搭起的简易门楼,门楼上隆重地写着“北京石油学院欢迎您”!

简易的校大门

建设中的教学楼
在我的想象中,北京石油学院应有宽阔的大马路,绿树成荫,高楼林立!而近前细看,却只见两栋三层高的南北教学楼和地质楼。学生宿舍也仅有“工字楼”和“五四楼”,其余都是大片大片的荒地和工棚,但晚间却灯火通明,建筑工人正在为我们打夯、平地,盖教学大楼和学生宿舍哩!

1955年国庆节前夕南教楼留影
我们入住的是“五四楼”(1954年建成的),我住在对着楼梯的大房间270室,8位同学,四张上下双层铁床,中间摆两张“一头沉”学生桌。楼道、室内外乃至门窗上,到处贴有“墙面未干”“小心!油漆未干”的字样,老师也叮嘱我们:睡觉时可别挨着墙面!
这栋“五四楼”里,东头(东西方向)住的是女同学,西头(东西方向)住的是男同学,楼正中间(南北向)住的是单身青年教师(都分别有厕所),就这样大家来来往往在同一层(座)楼,相安共处,既不需要出入证、登记,更没人把门,丝毫不存在“安全问题”,这和现在的学生宿舍楼对比,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!

1956年元旦,全班在54楼前合影
(二)先生讲课太生动
建校初期,由于教室、食堂不够用,需要轮流上课,开饭时间也要错开。比如,大清早5:30披星戴月就要到教室上课,上完两节后再回食堂吃早饭,8:00又需赶回教室再上四节,中午12:30吃午饭,下午一般上体育课、实验课或自习。
当年全院只有一座饭厅,楼下教师用餐,楼上学生用餐,拥挤程度可想而知,但秩序井然,还能安排8人一桌,四菜一汤。每月伙食费12元,绝大多数同学有助学金顶上去,靠着这国家补助的“免费的餐食”读完了大学。
我们上课主要在南教楼120的阶梯大教室,能坐150多人。上大课时,钻井三个班、采油两个班合班上课,为抢占前排的座位,就得起得更早!
印象最深的是讲《高等数学》的张希陆教授,他是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先生的长子,是留学归国的学者。张先生上课有一特点,从不带讲稿,但课讲得生动有趣,如在讲解析几何平面与曲面接触的关联点时,他做了一个比喻,提问我们:见过舞台上“丈八和尚耍大刀吗”?我们都傻了!他说:说时迟,那时快,大刀从额头轻轻掠过,丝毫不损伤额头,这就叫“切平面法”。多形象啊!逗得我们哈哈大笑!还有讲如何建立定积分概念步骤时,概括为“分区、取点、作积、做和、取极限”这11个字。这个概括,在我们做数学老师时,也将其传授给了学生!

北京石油学院数学教研室1964年元旦合影
张希陆教授:前排右5;卢名高:中排左5
(三)国庆游行最兴奋
初到北京,最兴奋的是参加国庆游行,接受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检阅。刚入学的那一年国庆前夕,我们新同学几乎每天下午都要操练走过天安门时的步伐,练习高呼口号。
“十一”那天凌晨4:00左右,由贾皞副院长带队,我们这群新生“小豆包”,每人背包里装三个小豆包和一个咸鸭蛋,整队集体步行到清华园火车站,乘上大闷罐车到西直门火车站,出站后步入西直门大街,经新街口、平安里一直到沙滩,沿途歌声嘹亮,口号声此起彼伏。
出王府井南口时,队伍开始密集,汇成20人一行的方队,情绪高昂地通过天安门广场。遗憾的是我们通过时,正好毛主席进入城楼大厅去了,队伍当然不能停步,但大家见到了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了,情绪仍然十分高涨。一直走到西单十字街口,出宣武门后,我们就在附近的一所中学吃午饭(肉菜包子是食堂师傅专门送来的)。休息片刻后,下午4:00重新整队,沿内城墙根(现在的宣武门大街)经供电局拐入有几座圆屋顶的国家银行,就到天安门广场啦!我们的队伍被圈定在中山公园正面偏西南向的一侧,广场到处红旗招展、人声鼎沸,悬挂在城楼上的大红灯笼更显得天安门壮丽雄伟!
华灯亮时,我们载歌载舞狂欢着。整个广场洋溢着宽松热烈的气氛,广场内可以自由走动,可离队加入别的队伍去狂欢,还可以进入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逛逛!
最使我们兴奋的是播放音乐停止时,突然礼炮齐鸣,焰火绽放,整个广场笼罩在一片金灿灿、亮晶晶的火花海洋中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夜景,兴奋极了!直到看完最后一次焰火,大约晚上12:00左右,我们才离开广场,又步行回到宣武门左边的那所中学“睡觉”去,实际就是迷糊一眼,因那所中学既没有床铺,也不可能有铺盖!
第二天不再组织集体返校,大伙便三三两两逛逛北京城吧!
(四)打响教学第一炮
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,1960年2月1日,开发系系秘书奚翔光通知我,下午两点到党总支办公室。我正点到达,总支书记刘永昌传达学院党委的决定:要我提前半年毕业,留校并转行当数学教师。
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,对于我既是鼓励,也是鞭策,更是压力。没想到,这一决定成为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,自此,我以教书为业,以石油大学为家,这辈子再也没有别的“岗”可上了!

卢名高毕业时在主楼前留影
一个星期之后的2月8日,我满怀激动地赶到数学教研室报到。当天上午阳光明媚,我们的到来也给教研室增添了一支新生力量。时任教研室党支部书记的程南熙同志为打消部分教师对我们的疑虑,并给予我们鼓励,特意在教研室欢迎会上强调:“他们是院党委从各系严格筛选出来的,是品学兼优、经受过锻炼和考验的又红又专的年轻人,希望各位老师热情地帮助他们,也希望这些青年同志向老教师学习,尽快过好教学关……”
当时给我的教学任务不重,只辅导一个教学班,但要求我们把早已忘掉的许多数学知识“捡”回来,还要加宽加深,熟练掌握全部内容。这是何等艰巨的任务啊!我只有铭记“要给学生一杯水,自己应储一缸水”的道理,鼓足“敢拼、敢搏”的勇气,虚心向老教师请教。在半年的时间里,我除了精读同济大学樊映川编的《高等数学讲义》外,还阅读了许多有关的参考书,如苏联名著吉米多维奇的《数学分析教程》等,并做完了《同济习题集》的2830道题。就这样,我在备课、答疑时心里踏实多了,不仅做到不胆怯,而且能熟练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。
当时,学院每个周六的下午和周三的晚上要开会,集体政治学习。为讲好每堂习题课,在周三晚上政治学习之后,我会继续“开夜车”,有时备课到天亮,洗把脸,吃了早点后就到课堂上课。下午或晚上,我便深入学生宿舍认真辅导,因此,尽管我的广东口音重,但同学们仍反映我的教学效果好。
为了让我们这批转行的青年教师尽快过“教学关”,教研室几位有经验的老教师轮流给我们上“提高课”,关怀备至地培养我们,爱护我们。特别是张希陆教授,他学识广博,治学严谨,有丰富的教学经验。时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,他身体很虚弱,但仍坚持每周给我们上一至两个下午的“提高课”,课后,他还把学生在学习中经常出现的疑难问题提出来,一一为我们分析和解答。对于教材中每一节的重点难点,每堂课内容的安排,都给出具体指导,从而为我们过好“教学关”提供了一条非常有效的“捷径”。
恩师的教诲和栽培给了我们信心和勇气,我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,经过一次次的试讲、讨论和教研室有关领导的检查、评定,认为我学习刻苦努力,教学认真负责,已具备开课的基本条件,同年9月1日就让我给1960级地质专业3个班主讲《高等数学》,成为这批青年教师中首位开课者。
“初出茅庐”就能得到同行的认可和学生的好评是很不容易的,因此,我更加努力,不断扩大知识面,曾先后到北京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山东大学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知名学府脱产或半脱产进修、深造。这样接下来又给1961级开发专业5个班主讲《高等数学》,教学效果同样得到教研室同行和学生的一致好评。就这样,教学的“第一炮”打响了,教学讲台站住了。
(五)赴大庆油田“苦战”
1961年4月初,根椐曹本熹副院长的指示:数学教研室要探索《运筹学》在石油厂矿方面的应用。据此,基教处(系)委派我带工经56级的6位男同学到大庆油田作有关方面的毕业实习。关于《运筹学》这个学科的知识,我们当时还是一片空白,为此先后到中科院数学所、北京工业大学学习、求教,搜集有关资料,做好去大庆的一切准备。
4月中旬的大庆仍是白雪皑皑,天寒地冻。当时仍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,但大庆人战天斗地,几万名工人、技术干部,忍饥受寒,干劲十足,热气腾腾地组织春季大会战。一开始我们被分配到大庆萨尔图一号院总调度室,在总调度长郑浩处长的领导下,我们每天跟车队跑运输,摸索运输调配方面的问题。当年的大庆还没有建起合格的公路,汽车在冻土上行驶,不时就陷进去,我们这些助手只好拿来铁锹、垫上石头,有时要耽误一两个小时,午饭都顾不上吃,但仍毫无怨言,一心扑在工作上。
记得有一次大休日,我们跟着石油工人开着大卡车,到一片野茫茫的草原上去采摘野生黄花菜充饥。没有灶具,只好用几块砖头,架上一个小脸盆,再用铁锹铲来一块原油(大庆原油含蜡量很高)就烧起火来。黄花菜味道鲜美,但我们不敢多食,唯恐吃多了中毒!
我们曾到铁人王进喜的1205钻井队蹲点,亲身领略了铁人的“有条件上,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”的革命精神。在一次班前会上,工人们席地而坐围成一圈,铁人站在中间,用他浓厚的甘肃腔布置完这个班的生产任务后,接着就“大刮”个别怕苦怕累工人的“胡子”(铁人的口头语,批评之意)。铁人的直爽和责任心,使我们受到莫大的教育。
王进喜1960年春到大庆,一下火车,步行两个多小时来到井场,就立即组织工人把60多吨重的钻井设备,人拉肩扛地运到井场;为处理好钻井的泥浆,亲自跳入碱性很大的泥浆池用身体当搅拌机;为大庆第一口油井顺利完钻,他七天七夜没离开井场,“铁人”一称由此而来。
2006年6月中旬,我有幸和当年开发大庆油田的井55级同学重返大庆,参观“铁人第一口井”的故址,这口井仍以每天自喷8吨油的产量继续为大庆作贡献,现已成为“大庆文物”。这里还落成了一座铁人王进喜同志纪念馆,馆前竖立着王进喜同志高大的花岗岩石雕全身像,馆内陈列着“铁人”生前辉煌的战斗事迹图片和实物。王进喜同志因忘我劳动,积劳成疾,患上胃癌,于1970年医治无效逝于北京,年仅47岁。我们在他的塑像前默哀并留影以示怀念!
我在大庆苦战了三个月,在队里的总结会上受到表扬,并被评为“二等红旗手”。7月初返回北京,撰写出了“线性规划在钻井运输方向的应用”一文。
从1960年2月参加教学工作站上讲台,至2007年6月放下教鞭,前后共47个春秋,听我授课的各类学生达4000多人,他们中有国内外知名度很高的学者、精英,大部分都成为各个领域、特别是石油行业的重要领军人物,可谓“桃李满天下”!
2021年“七一”前夕,在学校举行的表彰大会上,我和当年领我进入北京石油学院的李妙兰学姐,作为“光荣在党50年“的老党员,又相见了!
人老喜怀旧 翻阅老学历
追述在校事 晚年添乐趣